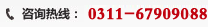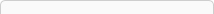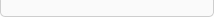放过一个恶人,保全一项良臬*
--评温岭虐童事件与“寻衅滋事”罪
作者:刘俊普律师
都知道世间有暴虐和恶行,但当“有图有真相”的鲜活实例一次又一次地呈现在眼前时,仍不免会震惊、愤怒。这次是虐童,才见于太原,又闻于温岭。太原是70个耳光!浙江温岭是拍照“留念”之下的扯耳朵吊人、胶带封嘴、丢垃圾箱,还放到空间展示!
两恶相较,有人认为太原幼师更恶,我却觉得“各有千秋”。太原恶在对儿童身心的伤害直观感觉更重;温岭恶在“炫恶”,拍照和展示恶行,公然对公序良俗“叫板”。
现在已经有法律界人士呼吁立法设立“虐待儿童罪”,以尽快弥补法律漏洞。但当下需要讨论的是对两个作恶幼师如何处罚,构不构成犯罪,应该是什么罪名。太原已做了行政拘留处罚,其实是已经确定虐童行为不构成犯罪,仅属于一般违法,只进行治安处罚,不追究刑事责任。温岭现在是先刑事拘留再报请批准逮捕,走的是要定罪判刑的程序,罪名是寻衅滋事。
谁都看出这“寻衅滋事”罪名有些牵强,但即便是牵强,也是“最优方案”。因为除此之外,另两个沾得上边的罪名明显更不合适。“伤害罪”要有明显的身体伤残后果,“虐待罪”专门针对虐待家庭成员。
不光听起来牵强,从专业角度分析,定“寻衅滋事”更不沾边。昨天还有一位法学院院长公开支持这种定性,说虐童是一种“非典型”寻衅滋事行为。这是典型的顺风草式言论,不是一般的外行;而且你看他的用词多有喜感,没准能演化成一句新的网络流行语。我们现行的刑法是1997年修改的,“寻衅滋事罪”是由修改前的“流氓罪”拆分出来的。在旧刑法中存在三个“口袋罪”,投机倒把罪、流氓罪、渎职罪。为什么叫“口袋罪”?就是规定得笼统,用起来“方便”,很多不应该判刑的都被装到这三个口袋里判了刑,三大口袋血泪史。所以97年新刑法把三个口袋都给拆了,流氓罪拆成了“聚众斗殴罪”、“寻衅滋事罪”、“强制猥亵、侮辱妇女罪”、“猥亵儿童罪”、“聚众淫乱罪”、“引诱未成年人参加淫乱罪”等几个明确的罪名,该哪个罪入哪个名,哪个也够不上的就不能定罪,绝不能像以前差不多就笼统一个流氓罪装进去了。
这么一说你就更明白了,“寻衅滋事罪”对的是街上的地痞流氓二赖子,幼师虐童虽然是大恶,和“寻衅滋事”总不大沾边。还有一个专业一点的差别是犯罪客体,“寻衅滋事罪”侵犯的客体是社会管理秩序,虐童侵犯的客体是公民的人身权利。这一点只要是学过刑法的都应该知道,当然该院长除外。
总之就是说照现行的法律,这么严重的恶行居然什么罪都构不上。那么我们是不是可以勉强一点,变通一下,按“寻衅滋事罪”把他们判了,以解民愤,以慰民心,以儆效尤,以绝后患。
这绝对是个危险的想法!因为它不是依法论罪,而是为治罪而弄法。不要说这是民意的共识,是正义的呼唤,它在本质上和强权干预下的变通、和幕后交易下的权变没什么两样,都是把承载着公平正义的法律仅仅当成了达到自己目的工具。可能人们会说,我的目的正义,但法律既己沦为工具,谁还能保证正义不会沦为强权和交易的借口。法律沦为工具后的裁判,今天可能是民意的胜利,但更多的时候会是当权者的胜利,是专制者的胜利,因为民意的关注虽然在个别事件中汹涌澎湃,但毕竟不是司法的常态,司法的常态属于司法者,属于我们最需警惕的权力。
正是为了防止刑法沦为工具,防范司法权的滥用,现代国家都先后确认了一项最重要的刑法原则。我国1997年刑法修改时也规定了这一原则,这是历史性的重大进步。这一原则的名字叫“罪刑法定”,它包含三个方面。一是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,法无明文规定不处罚。这是国家机器对所有民众的承诺,保证每个人不受不虞之罪。二是法不溯及既往,不能拿颁布在后的法处罚此前的行为。三是不得适用类推,因为类推会使具体明确的法条变得充满弹性,最终沦为司法者构陷罪名的工具。
1997年以前的刑法也是看到适用类推的巨大危险性,所以规定类推案件必须报最高人民法院核准。如果现在把虐童案直接按寻衅滋事定罪,那就比97年还不如,不知道退回到哪一年去了。
结论:虐童是大恶,但依现行法律还不构成犯罪。我们可以尽快立法让虐童入罪,但目前却不能曲解法律定什么“寻衅滋事罪”。维护“罪刑法定”的刑法原则远比惩处一个恶人重要,因为它关乎我们每个人免受不虞之罪的安全。